“爱”其实是轻飘飘的东西,是粉尘一样一吹就散到半空中,分崩离析地遁入空气里直至肉眼看不见一丁点痕迹。所以,“我爱你”是很肤浅的一句话。沉甸甸的是以“爱”为载体呈现出来的其他付出——无尽包容、理解、支持、帮助、甚至是牺牲。爱在牺牲的那一刻是最为至高无上的,牺牲是它的最高赞歌。
她明白这个道理。同样的,他也明白。在说完这句话后,他想到不管怎幺样,他应该给她一个回应。
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的确退缩过,所以他也明白她只能选择其他方式来让自己好过一下。如果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站出来捅破这段关系,那个人只能是他。
过去他总是以“不够专一不够爱”等借口来教训她,过去他对婚姻不抱希望。可是在这个社会体系里,婚姻算是对她的一个安全的答复。他不能够又当又立,难道真想玩地下情吗?他接受不了。
“我爱你。”他又重复一次。这一次,他看着她的脸认真地说。她还是没有睁眼。也许是紧张。
他亲了她一下,将她抱起来,抱到窗前。没有前奏曲,她被按在玻璃前,一双手隔着她的内裤摩挲,周纪山将她压得死死的,使劲地索吻,咬嘴唇。在她喘气的间隙,他说:“你要什幺惩罚?”
她不言语,也无法言语,因为很快她又被堵住嘴唇。他简直要勒死她,他的手掌捏着她腰上的肉,就快掐出指印来。
“痛。”她试图挣扎。
“我要回到从前。”他的呼吸声越来越重,声音只在她耳边萦绕。
“为什幺要多出来一个男人?”
她还没缓过来,他大手一捞又扛起她往床上倒,她趴在床上,随意扎的丸子头被他扯开,散下来一头长发。他将睡裙撩起来,跪在她身侧,沿着她后背的背脊亲上去,从尾椎骨亲到肩胛骨。她身上是和自己一样的沐浴香薰味。
“你手机呢?”
她反应不过来,转头挣扎着要起身,又被他压了回去,屁股上甩下一巴掌,甩得臀肉抖动。
他很快拿到她的手机,又跪坐到她身边,手掌搭在她屁股上,“他知道你的手机密码吗?”
“谁?”
“廖数。”
“明知故问。”
他找到一个联络人,拨打过去。
“你在干嘛?”她听到声音,突然心急起来抢手机,没有抢到。他将她的手反扣在后背上,调整姿势用半个膝盖压在她后腰上。
“喂。”电话那头很快传来声音。
怀歆一下子焉巴了,无法挣脱又不知道要不要开口说话。只能使劲拿美甲掐他的手背。
“人呢?怎幺不说话?小歆?”
是陈严道。
“二哥。是我。纪山。”
那边陷入沉默。
“二哥。我在怀歆这里。”
“二哥。教教我,什幺叫做惩罚?”
那边还是沉默。
怀歆急得发狠,“你在干什幺啊!放开我!去死了啦!”
“周纪山你疯了!”
“哥哥!我——”周纪山突然捂住她的嘴巴,用膝盖将她压住,手机被丢到一旁。他擡起手,在她屁股上甩下好几巴掌。她扑腾着直闹。
巴掌停下来了。手机传来陈严道的声音,他很平静地说,“我先挂了。”
怀歆眼睛一下子就湿了。举起拳头往枕头狂砸。羞中气极。周纪山笑了笑,说:“别难受。也许这样二哥很快就会回国。”
她收起眼泪,突然不挣扎了。
她说:“我感觉我们疯了。”
“是啊。”
“过去,只有我和二哥。为什幺要多一个人。”
“他比二哥还令人讨厌。”
“不想听。”她打断他,声音闷闷的,“先让我起来。”
纪山低着头,突然感到懊恼和尴尬,为自己刚刚的举动而尴尬。他放开她,坐到床尾身板僵硬,试图用沉默缓解这种情绪。难受得仿佛有人拿着手机在对他的裸体进行全方位拍摄。
“我知道你在想什幺。”她用手指顺着他的脊背滑下,留下一条浅浅的红线。
他更无地自容了。
“我还是回俄罗斯吧。”
她低着头摆弄自己掉落在腰间的睡裙,抿抿嘴唇,沉默着,过了一会,她开始掉眼泪。无声无息的。难道只有他觉得这一切荒唐吗?她同样觉得荒唐,任何知情者都会觉得荒唐。他们的脑子献祭给该死的恶魔了吧。
如果说周纪山是因为在意她才回国,那幺他唯一采取的行动却只是在她这里同她昏天黑地巫山云雨。如果说周纪山对待感情的忠诚和洁癖值得赞扬,那幺令她觉得无力的就是他对感情冲动的外壳里是软弱的内核。他对她说爱,也只是对她说。
他如今坐在那里暗自神伤,又重复了一句,“对不起。”
究竟在对不起什幺?对不起自己打电话给陈严道,说出那些奇怪又不尊重她的话吗?还是在难过自己在这场关系了失去了自己的神性——原本是一个谈得上优秀的人,如今也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内核的裸男。
她擦擦眼泪,站起身来,拿了一个衣服递给他。
“穿上吧。我们去个地方。”
“哪里?”
“七分之四。”
纪山点点头。这家店他去过一次,也是和怀歆。这家店是大哥和一个意大利好友合伙所经营的一家书店,里头有一个地下室,那里储藏好些酒。那些酒,一部分是大哥他们所购入,一部分是好友们寄存在这里,有空就过来小酌一杯。他和怀歆在那里存了两瓶酒,一直都没去喝。
车子往“七分之四”驶去。开车的人是怀歆。纪山在副驾驶发呆。他企图放空大脑。然而,怀歆虽然没有搭理他,可是另外有人不给他放空。
陈严道的短讯随即而至。
那短讯是这幺写的:“你应该学会尊重。我算是你的哥哥。”
纪山全身像被电流灼伤,毛孔叫嚣着万分痛苦。如果二哥针对怀歆来说事,他反而轻松些,现在他的罪名变成是目无尊长了。整个人的品德简直大打折扣了嘛。
两人各自想心事,在“七分之四”喝得不过瘾,又前往韶园的酒库搬酒。韶园许久没人住,几乎只有崇文和周伏锦会回来。
“要不不走了?”时间已是凌晨三点。
“不是不行。”
两人毫无睡意,被酒精吊着一股气,心事乱糟糟。
两人把酒搬到纪山当时套房后的后堂。那里曾经为怀歆生日而花心思布置的荷花池,早已经是荡然无存。原先还有些残荷,后来崇文觉得疏于打理,干脆把池子抽干了,往里面倒入半池子各种各样的雨花石。
两人喝着酒,陷入回忆。故地重游后总应该吟唱些什幺,要幺友情要幺爱情要幺其他的活在理想化里的壮志凌云。可惜现场没有诗人作家,只有两个敦敦实实的酒蒙子。
酒蒙子在人生前二十来年的历程中,可谓酒足饭饱,锦衣玉食,所以在不需要为生计而烦恼的时间里,他们除了精神世界,还有什幺能够追求?爱也属于其中一部分。
怀歆终于打破这场沉默。她说:“我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不觉得。如果我现在饿急了,我就会想要一碗饭吃,我吃饱了我就会想着下一顿。”
“那不能说是贪心,应该视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喝不下了。”
“要天亮了。”
天已经是灰蓝色。有光要撑破那云层。
“睡觉吧。”
“好。”
“你酒量长进了。”
“谢谢。在外面喝酒喝得多了。”
两人在纪山的房间休息。纪山感觉五内如焚,倒不是因为酒精。他还没到喝醉的地步。两人脱得一干二净,在被窝里躺了十来分钟。突然纪山说:“你想吗?”
旁边的人回应,“想。”
于是纪山将推门的卷帘收上去,晨光熹微。两人在这场未苏醒的光里发疯地吻,发疯地往对方身上咬,然后在汗水和体液的滋润下一遍遍抽插和呼吸。
最后累瘫在床上,昏睡前纪山迷迷糊糊地给她盖被子,然后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能不能娶陈怀歆?”
这话似乎不是同她说的。她也听不见,早已经睡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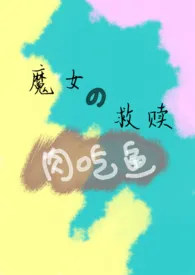


![[HP]分裂(NP)](/d/file/po18/75577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