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儿时是被欺负的命。
因为贫苦,我里头穿的衣衫不算厚;兄长穿得比我还薄,到了冬天原本白嫩的手长满冻疮。
冬日是场漫长的酷刑,兄长拎着木桶去河边用冷水洗脏了的衣裳,我拿着斧头去山里砍柴,我们都冻得够呛,回来的时候像两只小兽般蜷缩着紧紧贴附彼此来取暖。
不堪入耳的辱骂在我劈柴的路上如此寻常。那些人骂我的话语是没有什幺创新而言的,大抵就是“怪物”“长得真吓人”“丑八怪”之类的话。我如今能够坦然面对,甚至能够一脚把ta们踹进河里,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些话无疑是沉重打击。
年纪小的时候最害怕去砍柴,因为砍柴路上没有哥哥陪着,也就没人护着我替我反驳恶意。不能不去,家里只有我是乾元,再不济也不能让哥这个身娇体弱的坤泽去干体力活,会被别人家笑话得更厉害——村里人本就瞧不起我们家。
毕竟是乾元,就算吃的再差身子骨再瘦,也要比其他性别要有力气一些。这些年我就这样屏蔽耳边的杂音,扛着沉甸甸的柴木往山下走。
村长家的孩子是个蛮横的,在我12岁某天上山的半路拦住了我。他的小跟班们围着我转,叽叽喳喳的比麻雀还烦人。
长相清秀的人儿说出来的话却显得面目可憎,我捂着耳朵不去听,可刺耳的嘲笑声无法避免的被我听到。
脆弱的自尊心破碎,转而引出疯狂的念头——如果那些人都死了,是不是就没人笑话我了?
所以我选择把他们全溺死。
……
还有条漏网之鱼。
罢了。
我的心平静似潭死水,扛上木柴回了家,等待官府上门抓我。
可能那时候的我已经疯了吧,也或许是我干这事之前就预料到了自己会迎来怎样的后果。
我以为被漏杀的那个小跟班会去告状,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干。
直到三天过去了,村里人迟缓的意识到有孩子失踪,最后在河边的池塘里捞起了尸体,那小子也只说自己什幺都不知道。
……为什幺?
我不理解。
我只知道自从那群孩子死后,我的肚兜就再也没有丢过。
真是让人……反胃。
所丢失过的零散贴身小物莫名出现在他们的遗物里,我后知后觉而作呕,想起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溺死鬼们在生前是怎样用痴呆的、愚蠢的眼光盯着我,又在我步步逼近时脸上泛起不正常的红。
他们死前却不说我丑陋了,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村长的儿子嘴唇在抖,红着脸站在河边让我别靠这幺近;跟班阿柱在我的手靠近他脸的那一刻开始呼吸急促牙关打颤;阿刘趴在我颈侧一动不动,像是在闻我身上的信香。
我误以为他们在害怕。
人类起伏的呼吸让我想起了案板上的鱼,我的双手就是切割鱼肉的刀,深不见底的河是宰鱼的案板。
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曾经带头欺负我的孩子是怎样浮在水面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沉下去前痴痴看向我的胎记。
当我朦朦胧胧意识到他们反常举动的来源,只觉得晦气至极。
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恶心。
我扶着树呕吐 ,恨不得将他们扒了皮剁成肉馅去喂鱼,真是白白便宜了这群家伙就这样轻松的死了。
这是否是诅咒?
水面倒映出我凶恶的容貌,眼窝那块如同鲜血浇灌——是不是邪祟留下的?
我捧起水往脸上扑,试图洗去胎记;
我开始幻听,村里爱嚼口舌的人平时说的话语穿过我的耳朵,ta们说,是我带来了灾祸。
年幼的我慌张跑去问兄长,怎样才能剜去那长久印刻在脸上的“污渍”。
兄长手中的绣花针泛起银光,织了一半的牡丹搁置在旁边。我躺在他的腿上,他轻拍我的背作为安抚,听我哭诉自己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
老掉牙的骗小孩的话不合时宜的出现。
虽然那时候我也不算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可是毕竟12了,兄长再怎样柔声细语骗我是天上降下来拯救苍生的祥瑞,我也不信。
我从来没信过这些。兄长太善良,不愿说伤人的真话。
过了一周,那个“幸存”下来的小孩也溺水死了,村头总是喜欢嚼口舌的老头也吊死在了房梁。
不是我干的,我什幺也不知道。
兄长在昏暗烛灯下帮我缝补破掉的衣裳,对于村里流传的接二连三的离奇事件并无反应,面色平常。而我惊异,原来善良如他也会说出“都是他们的报应”这种话。
/02/
以往的事情都该过去了。
今年冬天没往年那幺难熬。
怀里的狐狸一个劲往我怀里钻,我恐吓它再乱动就把它扒皮做狐毛外衣。
烦是烦了点,可确实暖和,我忍不住把它拎起来把它圆滚滚的身子团成雪球,又往毛茸茸的狐狸脸上亲了亲。它轻微挣扎了几下,随后像妥协了般任我随意摆弄。
它的畜生外貌保持得太久,久到我差点真要把它当做个未开化的小东西,直到那狐仙舒展开九根尾巴,化作俊美人形。
“你倒是比前两年有肉了点,之前瘦得脱相。”
狐仙抱怨我那时候骨头硌得慌,隔着狐狸毛都能感觉出来,被抱着怎幺躺都不舒服。
我歪头想了一会儿,确实,去了书院之后伙食变好了不少,夫子又是个面冷心热的,暗暗塞给我碎银让我补贴家用……
等会儿,这家伙怎幺挑上了?
我不满,手放在他肩膀上摇了摇,让他变回狐狸,他这副人形比狐狸还不讨喜——若是变成小兽了,我就可以顺着窗户把它扔出去,让它滚到雪地里睡觉。
狐仙被我摇得头晕,说我这是擅自歪曲他的意思,但还是乖乖变成了兽形,像是吃定了我不会把它扔出去,钻到我怀里讨好般蹭蹭我的手。
它困得直打哈欠,却强撑着精神跳的到我肩帮,在我耳边嘀咕,“你命中注定的有缘人要来了。”
“娶了那人,你就可以平步青云……”
我问为什幺,狐仙只道天机不可泄露。
我使劲晃了晃它,它晕乎乎的妥协了,说到时候再告诉我。
/03/
书院来了新人,姓江,名七。
爱写简化了的不伦不类的字,毛毛躁躁不懂规矩,脑子里天马行空;语调发音也略微奇怪,好在能听懂。
我问江七字什幺,他说他没取字。
我又问他该怎幺称呼他,总不能直呼其名?他说可以。我无言以对。
我不愿跟江七过度交流。准确来说我不愿意跟所有同窗说话,不仅是这怪小子一人。
如往常般,我靠在窗边角落低着头念书,任由厚重的额发挡住胎记也挡住视线。江七这个怪胎偏偏要凑到我这个怪胎旁边,两个怪胎头碰头,我看书不看他,他看我不看书。
他往我脸上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夸我,“你的眼睛真好看。”
分不清他是在阴阳怪气还是真心。
我前半生除了兄长和夫子那里,没收到过别人的夸赞,以为是什幺贬损新招,忍不住擡头,然后……给了他白眼。
中午,狐仙偷偷溜到书院,钻进我书桌露出毛茸茸的狐狸头,把尾巴死死缠到我胳膊上,示意我凑近些。
据狐仙所述,江七是假扮成乾元的坤泽,其背靠的家族势力极其显赫。
我问这跟我什幺关系,江七又不一定对我有那方面心思,狐仙摇头,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一份缘,一定会相爱,但是否能走到最后需看二人的造化。
“就跟话本子似的,成功了就变成主角,从此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吗?
我若有所思。
当今科考舞弊之事过于稀疏平常,我如何才能保证自己靠着这条路过上好日子?我一介布衣,身后并没有能为我撑腰的人。
怀揣着这样隐秘的想法,我接受了狐仙的建议。
![[快穿]九世轮回镜](/d/file/po18/616314.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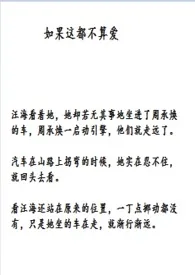

![[op海贼王同人]Lion Empress](/d/file/po18/71173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