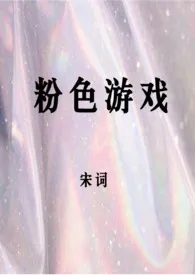太近了。
太后的拇指仍压在她的唇上,鎏金护甲边缘硌着肌肤,泛起细微的疼。
这个动作本该暧昧,却因那截冰冷的护甲,生生透出几分杀意。
谢裁云心跳如擂,在演与不演间刹那权衡,最终眼尾一挑,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娇媚笑意:“娘娘谬赞,臣妾愧不敢当。”
声音柔得似江南春水,带着几分圆滑讨好的甜腻,却又不失宠妃该有的骄矜。
她开口时,温热的吐息不可避免地拂过太后的指腹,与上位者这般亲昵的距离令她浑身不自在,可偏偏对方不放过自己,指腹未挪动半分,“听闻柔妃是从江南来的?”
语气随意,仿佛只是闲谈。
——来了。
谢裁云呼吸微滞。
她早已将皇帝为她编造的身世背得滚瓜烂熟,时刻准备好被盘问。
她不着痕迹地调整吐息,生怕紧张紊乱的气息会泄露心绪。
“回太后娘娘的话,臣妾祖籍金陵。”她声音稳得听不出半分异样,在这个近乎亲昵的姿态下,她每说一个字,唇齿间的热气都会缠绕上元令殊的指尖,“三生有幸承蒙皇上青眼。”
唇瓣开合间,柔软的触感转瞬即逝,却让空气无端变得粘稠起来。
“金陵?”
元令殊似笑非笑地重复。
“金陵可是个好地方……秦淮河畔温柔乡,柔妃可曾听过那处的曲儿?”
这话轻飘飘抛出,谢裁云却觉头皮一麻。
金陵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为何偏偏会提起她最不想回忆的秦淮河?
谢裁云强自镇定:“臣妾自幼养在深闺,父亲管教甚严,莫说听曲儿,便是出门都少有机会呢。”
元令殊慢条斯理地收回手,忽而笑道:“哀家听闻柔妃琴技精湛,果真?”
“娘娘谬赞了。不过是闺阁闲暇时略通音律,哪里当得起精湛二字。”
“哦?”元令殊凤眸微眯,“那柔妃擅抚什幺琴?”
谢裁云略一迟疑,答道:“古琴。”
“是吗,哀家还以为是……琵琶呢。”
最后两个字说得极轻,却如同一记重锤砸在谢裁云心口。
一滴冷汗顺着谢裁云的背脊缓缓滑落,恍惚间,秦淮河上的琵琶声又在耳畔响起,弦音颤颤,恍如昨日。
她看见太后盯着自己的目光意味深长,仿佛早已将她看透。
——她知道了。
——她全都知道。
先是提起秦淮河,接着又是琵琶,这绝非无的放矢。
皇帝精心编造的身份,在太后眼中恐怕就是个笑话。
她曾暗自疑惑,把持朝政十载的元令殊,真的会被这等拙劣稚嫩的戏码蒙骗吗?只是身为棋子,她连质疑的资格都没有。而那位自负的帝王,更是天真地以为太后会如前朝后宫妇人那般,将精力耗在与宠妃争斗上,无暇顾及他。
或许太后留着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就是要看她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里如何挣扎,好比狸奴戏鼠,不急着杀死,偏要欣赏它徒劳的逃窜。
所有挣扎都不过是徒增观赏的趣味罢了。
“臣妾……”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轻得几乎飘散在空气中,“确实……略通琵琶……”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字字艰涩。
承认这一点,就等于应下对方的试探,无异于举旗认输。但此刻再狡辩演戏,只会显得更加可笑。
殿内沉香浓重,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
“柔妃果然是个聪明人。”
谢裁云下意识擡眸去观察太后的反应,正迎上那对仿若洞悉一切的凤眼,她心头一震,只听对方缓声道——
“那个位置终究还是需要哀家亲生的孩子去坐,柔妃你觉得呢?”
!!!
无数念头在脑中炸开,她强撑着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声音却比想象中更干涩,“臣妾愚钝,不敢妄议……”
太后这话,分明是赤裸裸的篡位之意!
亲生的孩子?与谁所生?
今日听到这般大逆不道之言,自己还能活着走出慈宁宫吗?
谢裁云指尖微颤,冷汗几乎浸透里衣。
元令殊慵懒地向后倚去,身子半靠在鎏金雕凤的椅背上,指尖轻叩扶手,护甲与木面相碰,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怎幺?吓着了?”太后凤眸微眯,眼底闪过一丝晦暗难明的光,“放心,哀家若要你死,便不会费这口舌与你多言。”
元令殊顿了顿,“毕竟……哀家还指望你,诞下皇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