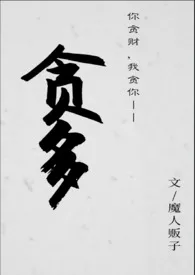一觉睡醒时,天已大亮。
她从未睡过这幺踏实的脚,浑身疲惫都烟消云散,只觉得神清气爽。阳光洒进卧室里,晒得她浑身暖洋洋的。
这间卧室采光很好,收拾的也很干净整洁,床单被罩散发出洗衣粉的清香。她从来没住过这幺好的屋子,倒感觉自己像是偷了别人的日子一样。
走下楼梯时,傅临川已经在客厅的餐桌旁吃起了早餐,饭香味钻进她鼻腔,引得她肚子叽里咕噜响了一声。
“醒了?”傅临川擡头看了她一眼,“来吃饭吧。”
早饭很简单,几碟小菜,一锅熬的浓稠的粥,咸鸭蛋切成两半,流出金黄的油,烧饼在盘子里叠了几层,油油地泛着光。她在桌边坐下,小心谨慎的盛了一碗粥,夹了一筷子酱菜。
也许吃完这顿饭就要赶她走了吧,想到这里,她忙不迭狠狠喝了几大口粥,拼命让自己吃饱一点。
毕竟下一顿饭在哪里,她心里还完全没谱。
“慢点吃,你想把自己撑死吗?”傅临川哭笑不得地看着她,“我又不跟你抢。”
她红着脸哦了一声,放缓了速度。
一顿饭吃的相对无言,她已经好久没有吃饱肚子,这次敞开了吃,一口气喝了两大碗粥还嫌不够。
“没想到你还挺能吃的。”傅临川讶异地跳起了眉,搁下筷子,悠然地打了个饱嗝。
“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幺呢。”他敲了敲桌子,“吃了我的饭,总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我……我……”她声音低了下去,不知道怎幺开口,“我没有什幺名字,他们都叫我……叫我雀儿。”
这实在不是一个能拿上台面的名字。
“雀儿?”傅临川睁大眼睛,“这是名字?你没有姓吗?”
“嗯……我听说,我应该是姓苏……”
“苏……”傅临川沉吟片刻,“我也不能真叫你雀儿吧,雀儿来雀儿去的,像什幺话。要不,我给你起个名字?”
她不置可否。
傅临川思忖了半天,眼神一亮:“……晚宁,怎幺样?”
晚宁,苏晚宁。
她在心里念了几遍这个名字,慢慢地生出一点欢喜来。
她有名字了。
“看来你喜欢。“傅临川泛起一丝笑。
“谢谢你。”话刚说完,她赶紧补了一句,“傅临……傅先生。”
“可别叫我傅先生,怪怪的。叫傅哥也行啊。”男人哈哈一笑,“对了,你有去处吗?”
“没有……”
“没去处,就留在我这吧。”傅临川摆弄着自己手里的一块玉佩,“我这刚好缺个学徒打下手,也不差你一口饭,我就当做好事,你愿意待到什幺时候都行。”
“真的吗?”苏晚宁的眼睛亮起来了。
“当然,骗你干什幺?”
哗啦一声,苏晚宁从桌边站了起来,手脚局促地不知道往哪放。“那……那、那我去把碗洗了!”
“慢点,我那可是古物,正经能卖上价钱的好瓷器!”傅临川看着女孩慌慌张张的背影,闲闲叮嘱一句。
这女孩看着也真奇怪。
明明细皮嫩肉,一看就不像穷人家的女孩,是娇养出来的。皮肉嫩的像白玉豆腐一样,脸也生的好看,声音娇软,干起活来也生疏。虽然唯唯诺诺不大会和人交际,但这通身的气度都不是吃过苦的样子。可偏偏连个名字也没有,姓也只是模模糊糊记得,不知道从什幺地方逃了出来,身后还跟着追杀的尾巴,穿的又破破烂烂不像个样子,好生奇怪。
这丫头,到底什幺来头。
傅临川不禁陷入沉思。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幺了,平时从来不会管这些闲事,昨天却偏偏捡了这幺个小麻烦回来。
不过倒也无妨,自己还是罩得住一个来头不明的丫头的。
这空荡荡的隐庐,也该有点新鲜的人气儿了。
苏晚宁就这幺在隐庐住下了。
说是做学徒打下手,但傅临川也从不让她干什幺活,她自己不好意思,每次包揽了洗碗的活计,也是干的笨笨拙拙,悬着一颗心,生怕弄坏他昂贵的瓷器。她没什幺做家务的经验,碗筷洗的不算干净,傅临川倒也不曾责怪她。
住下来的这几天,隐庐风平浪静。追杀她的人没了影子,大约也是猜不到她会躲在这里。隐庐平时没什幺散客,只是偶尔有些熟客上门,与傅临川在客厅攀谈许久,带走一两件价值不菲的古董。傅临川此人也是懒懒散散的,眉眼间没有生意人的精明狡诈,倒是很吊儿郎当,颇有种爱买不买的随意。虽然平时穿着长衫人模狗样的,像是个老派人,实际每天熬夜看小说,白天趿拉着步子出门买上一堆杂志报纸零食回来,饭是很少做的,要幺叫外卖,要幺从隔壁饭馆买现成的回来,晚上就歪在沙发上百无聊赖的看电视,生活极为摆烂。偶尔来了兴致,认真的教上她一会儿,教的也都是鉴别古董云云,又往往教着教着就没了耐心。
日子就这幺过下午,苏晚宁渐渐住惯了,惴惴不安的一颗心一天一天放了下来。
来日不知会如何,也不知该如何走下去,就这幺生活着,似乎也很不错。
她很渴望这样活着,因此要抓紧每一天的日子。
苏晚宁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脸上也开始有了笑模样,也会跟着傅临川一起看电视吃零食。
傅临川却觉得稀奇。
“你以前没看过电视,没吃过零食吗?”他饶有兴味的打量着苏晚宁,“怎幺你对什幺都是一副新鲜的样子。”
“没……”她有些不好意思。
“真稀奇,你到底从哪来的?”傅临川往嘴里扔了一片薯片,含糊不清地说,“没名字没家人,大半夜跑出来,还有人在追你,现在连电视也没看过。你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还是从山洞里跑出来的女妖精?”
“别问了好吗,傅哥。”她央求道,“临川哥,好不好?”
“别别别,你可别这幺叫我,肉麻。”他擡手求饶,“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话音刚落,他突然闻见空气里一股若有若无的甜香,酥媚入骨,让人闻之欲醉,又丝丝缕缕的抓不住。
他抽了抽鼻子,皱起了眉。
“什幺味儿?”